甘建华 从茫崖吹过来的风 ——读顾锁英散文新著《漠风吻过南飞雁》
顾锁英老师曾嘱托我为这本书作序,彼时因手头事务繁冗未能履约,至今心中仍存几分歉疚。半年前收到样书,我即开卷展读,心潮难平,遂成短诗以贺:
天外茫崖吹过来的风
大西北最凛冽的白毛风
到了江南
就成了和煦的风,洋溢温情的春风
虽然至今缘悭一面
但我知道,青海与新疆交界处
茫崖石棉矿
曾有一个常州女教师的美丽传说
那儿是阳关外的旷古大荒
命运,曾将你托付给噶斯口
迅疾奔突的罡风,从而
浑身长满比玻璃陨石还硬的筋骨
而我也从未想到,这世上
竟然会有一本以写我的文章篇名
作为书名的个人散文集
可叹我们,都是被漠风吻过的南飞雁
顾老师年长我十岁,1984年至1999年在茫崖石棉矿中学执教语文。因为茫崖是我们共同的第二故乡,我始终以“大姐”相待。若论“柴达木才女”这个称谓,她当属最贴切的人选之一。据其自言又名顾凡,江苏常州金坛人,既是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亦是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。散文《寻觅遗失的白杨花》入选2017年度“中国西部散文排行榜”;摄影作品屡屡摘取省级奖项,1996年参与创作《青海资源系列折页》获中央外宣办、国务院新闻办“七个一工程”二等奖;油画与水粉颇见功底,代表作有《茫崖道班》《荒原》《大漠牧歌》《西部筑路工》《矿山就是我的家》等。虽然有人质疑网传其画的拍卖成交价,却也认为曾在柴达木盆地工作、生活的男画家,鲜有谁的作品能与之颉颃。如今,她将十六载盆地岁月凝结成书,既是个人生命轨迹的记录,更是茫崖石棉矿一代人的精神画像。
她的文字里蕴含着对盆地最赤诚的告白。在《苍茫之崖》一诗中,她写道:“青新交界处的大风口/飞砂扬砾的异乡/我用青春做过赌注//在洪荒中耕植 等待收获/在远古的风尘中 辨别方向/在无雨的空间 期待春暖花开”。这首诗恰是她在茫崖生活的缩影,以江南女子特有的细腻与温婉,在“风库”的凛冽与矿尘的厚重里,硬生生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“绿洲”。
茫崖镇地处柴达木盆地最西端,距离省会西宁1300公里,堪谓“青海省西部门户”。它的海拔高度3100米左右,夹在阿尔金山系阿卡腾能山与昆仑山系祁曼塔格山之间,东接花土沟镇,西去南疆若羌。此地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,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,风能贮量(有效风能)居全省之冠,极端风速达39米/秒,风卷砂石能将车皮打成弹坑。年均温1.6℃,昼夜温差20℃,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6.4℃,一年至少240天要生火炉取暖。“围着火炉吃西瓜”纯属奢望,“风刮石头跑,六月穿棉袄”的俗语则绝非夸张。
再怎么能掐会算,我也没有料到自己会与边城茫崖发生联系。而其异常严酷的生存环境,四十多年过去了,依然令我畏葸胆怯。那是1982年7月,我作为青海石油管理局西部职工子弟学校应届毕业生,前往茫崖镇考点参加高考。花土沟的条件就够艰苦的了,我们家好歹住的还是砖房四合院。谁知到了茫崖镇,举目一望,天哪!房子在哪里?一脚踩到人家的房顶上,原来都是地窝子。时令已是夏天,男男女女却包裹得严严实实,头上要么戴着棉帽子,要么围着大毛巾,个个捂着大口罩,相互间说话就像特务接头对暗号。
即便如今通了火车、飞机和高速公路,茫崖镇的交通仍然算不上便捷,因为它离周边城镇太远了。20世纪80年代前期,茫崖镇管辖着花土沟石油基地。油田上的人去茫崖镇办事,需往西跋涉七八十公里,途中饱受砂石路面的折腾,回来腰腿疼痛得休息一两天,才能缓过劲儿来。油田野外小队干部教育调皮捣蛋的青工,只需说一句“赶明儿送你到茫崖石棉矿锻炼两个月”,对方就会立马认怂。当地生活物资全靠从甘肃敦煌或新疆若羌运入,“一块砖、一颗螺丝钉都带着外地的温度”。
可就是这样一片“生命禁区”,却因石棉矿而焕发荣光——1958年5月,地质部632队九分队在乌孜别克族向导木买努斯・伊沙阿吉的协助下,发现了依吞布拉格山的大型露天石棉矿。同年12月20日,柴达木工作委员会派出张守义带领小分队,23个人扛着17把铁锹、十字镐和筛子等简单劳动工具,用极其原始、非常落后的方式,在荒无人烟的山下挖出第一筐石棉。此后数十年,“中国茫棉”声名鹊起,累计探明储量超2100万吨,占全国总储量三分之一以上,占全世界总储量十分之一强。年产销量早已双双突破10万吨大关,产品远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,成为国家建材工业的重要支柱。
荣光背后是难以想象的牺牲。网上有帖子称:“这是一个所有人不敢做深呼吸的地方,空气为石棉尘埃污染,居住区与石棉矿分离厂、堆积如山的石棉矿渣相邻。而墓碑一概朝东的坟场近在咫尺,让人总要联想起长眠砂土堆下的亡者,与空中弥漫的石棉尘埃有着必然的联系。”1992年9月,海西州作家井石到茫崖石棉矿采访,冯跟定矿长从采矿点回来时,“极像个刚出工间的弹棉花匠人,满头满脸沾满了棉尘。他嘴里说着‘对不起’,朝我们歉意地笑笑,又拿着毛巾出去,扑打了好一阵子,才使自己恢复庐山真面目。”2012年6月,上海电视节首映朱宇执导纪录电影《造云的山》,展现茫崖石棉矿工人真实的生存状态。那些在恶劣环境中劳作的人们,虽然过着艰苦卓绝、与世隔绝的生活,却没有失去他们的快乐,因为他们依稀看得到生活的希望。这部片子获得国内外许多个奖项,我是泪眼模糊地看完的,边看边想起一则真实而心酸的笑话。据说有不少茫崖石棉矿人的心愿,就是攒够了钱之后,在花土沟镇上买一套房子,而花土沟人最大的心愿则是逃离花土沟。
顾锁英散文虽未直接涉及这些沉重的话题,却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矿工家属的日常:土窑洞教室里的粉笔灰、沙尘暴中护着学生的教师、深夜暗房里冲洗照片的灯光,这些令人含泪的细节,让我读懂茫崖的每一寸土地,都浸透着建设者的汗水与坚守。
顾锁英曾在《天边的云》诗中吟咏:“许多年 许多日子/不曾有过闲暇/眺望 命运前定的茫崖//浩瀚的苍穹下/但见一只鹰 破云飞过”。我理解此处的“鹰”,其实就是诗人自喻。而其散文最动人之处,则在于“以小我见大我”——从个人经历的碎片里,折射出茫崖石棉矿一代人的生活图景。
《海鸥——我人生岁月的航标》一文,堪称顾锁英的“摄影奋斗史”。其时茫崖石棉矿近万人的单位,竟然没有一家照相馆,学生拍毕业照要坐车跑到花土沟。这种难堪与不便,让她萌生了学摄影的念头。1986年回江苏老家探亲时,她用同事托买衣服的余款,咬牙买下一台海鸥4A双镜头反光照相机,回程时用衣服裹了一层又一层。在兰新线柳园站下车后,又是两天汽车颠簸,她始终将相机抱在怀里,“怕它受一点伤,像护着自己的孩子。”回到家里,她把卫生间改成暗室,用铁架、纸壳做摄影灯,白天教语文、当班主任,夜晚在暗房里摸索冲洗、放大技术,有时只睡两三个小时。
沙尘暴围困的经历,成了她与相机的“生死契约”。一次外出拍照时,突如其来的沙尘暴。把她困在路边沙坑,鼻青脸肿间,她首先摸的不是自己的伤口,而是怀里的相机。“过后掏出‘海鸥’,它安然无恙——那一刻的欣慰,比拿奖还开心。”正是这份难得的执着,让她的镜头里有了《高原学子》的纯真、《西部希望》的炽热,也让她获聘为省级媒体特约记者,进而成长为一名高级摄影师。
若说“海鸥相机”是她与西部绝境抗争的武器,那“白杨花”便是她柔软内心的寄托。在《寻觅遗失的白杨花》一文中,她写下在德令哈等待工作调动的38个日夜:旅店外的白杨树飘着飞絮,像塞北的雪花,一个劲儿地涌进饭馆、钻进窗缝。这个在茫崖“见惯了风沙不见绿”的江南女子,小心翼翼地把白杨花装进口袋,视作孤独时光的慰藉——可离开时匆忙间遗失了那袋花,这份遗憾竟成了她多年的心结。“我托司机找过,给友人写过信,可再也找不回了。”文字里的怅惘,藏着的是盆地生活的苦涩与对美好事物的珍视,也让我想起自己在柴达木遗失的那些小物件——它们早已不是物品,而是与这片土地的情感羁绊。
2025年早春时节,《漠风吻过南飞雁》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后,顾锁英在全国16座城市开展赠书活动——徐州的老矿工聚集一堂,倾听老矿长周振海回忆当年开采的艰辛;茫崖市实验小学的师生捧着书本,诵读《茫崖情思》里“老师,我永远忘不了茫崖的母校”的句子;滁州的老矿工翻看着书页,缅怀当年在依吞布拉格山下奋斗的青春……
这场跨越几千里的“书香传递”,让我看到该书的价值,其实早已超越文学本身——它成了茫崖人的“精神纽带”。如今的茫崖,因翡翠湖、艾肯泉、千佛崖、油砂山、黑独山、胭脂山、阿拉尔草地等成了网红打卡地,游客惊叹于它的自然风光,却少有人知晓背后的工业历史。而顾锁英的文字,恰是打开这段历史的钥匙。它让人们知道,这个地方曾是无数人奉献青春的“战场”,那些土窑洞、老矿坑、海鸥相机,都是柴达木精神躬身践行的见证。
我的老东家青海石油管理局,与茫崖石棉矿虽然同在柴达木盆地西部,却因生产性质分属国家不同的部委,两个单位及附属人员并无多少往来。我迄今唯独见过一位石棉矿作家,就是曾任矿党委宣传部部长何平。其时是1990年夏天,青海省作协在互助北山林场举办读书班,我们两位来自盆地西部的文字工作者一见如故。早几年联系上退居成都的老诗人任炳荣,1964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,曾任茫崖石棉矿工程师室主任,后来调到青海省商业厅工作,晚年写过许多怀念与赞颂茫崖石棉矿的诗歌,我们却也从来没有晤面。顾锁英曾给我寄赠一本《五色石文学作品选》,是《中国建材报》文学副刊版1994年出版的结集。其中收录茫崖石棉矿五人五篇:散文三家分别是顾锁英《茫崖情思》、杨捷《茫崖的风》、何韶《大漠深处》,还有罗生智小小说《续弦》、周冰诗歌《茫崖魂》,可惜这五人我都不曾见过。
回忆我与顾锁英大姐的交往,都与柴达木的文学事业相关。2020年策划《在那遥远的地方——离开青海情系高原海内外诗人专辑》,我第一时间想到她,将其纳入轰传诗坛的36家诗人之列。2023年编选中国第一部同题文化地理散文选本《天边的尕斯库勒湖》,收录了她的《走!咱们去看尕斯湖》——那篇文字里对尕斯库勒湖“绿浪翻滚如大海”的描写,让我仿佛又站在湖边,聆听黑颈鹤的啼鸣划破大荒的寂静。再就是茫崖市第一部地理诗选本《云彩里悬挂着昆仑山》,收入了她与任炳荣二人的诗作。去年编选《西望花土沟》这个散文选本,将其写在下甘某的得意之作《漠风吻过潇湘雁》收入其中。未曾料到的是,她竟将此篇标题移植成了本书的书名——这份情谊叫我如何消受得起!
回过头来细想,顾锁英缀玉联珠的文字,可谓柴达木文化图景的一块重要拼图。不同于男性作者对盆地宏大叙事的书写,她更擅长从女性视角捕捉细节:课堂上学生冻得通红的小手、暗房里显影液的味道、沙暴中护着相机的臂膀、草丛中窃窃私语的小鸟、遗失初夏白杨花的怅惘……这些细节让茫崖不再是“艰苦”的符号,而是有温度、有情感的“家园”。
倘若从国际视野来看,茫崖石棉矿曾是中国工业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——“中国茫棉” 远销海外,承载的是新中国建设的力量;而今顾锁英的《漠风吻过南飞雁》,则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西部开发的人文之窗。
放眼全球范围内,工业遗产的保护与记忆传承已成潮流。茫崖石棉矿2020年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,而顾锁英的文字,正是对这份遗产的“软性记录”——它不像史料那样冰冷,而是带着个人体温,让读者看到“工业遗产”背后的人:那些在矿尘中坚守的矿工、在土窑洞里授课的教师、在沙尘暴中护着相机的摄影师……这些个体的故事,能引发不同国家读者的共鸣——因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、对艰难处境的抗争,是人类共通的高级情感和精神追求。
自从十年前在《花土沟的梦》一诗中,我说G315(西宁—喀什)是“这条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”,如今的茫崖市被游客纷纷赋美,正以“最孤独的网红城市”吸引大众目光。当人们为沿途风光而惊叹时,若能翻阅《漠风吻过南飞雁》,便能读懂这片土地的“双面性”:它既有自然的壮丽,更有人文的厚重。顾锁英的文字就像一位“资深向导”,带着读者穿过风光的表象,触摸到茫崖的灵魂——那是一代代人用青春、汗水甚至生命,在“风库”里种下的“绿洲”。
合上书页时,窗外的风正吹过雁城衡阳的街巷,可我仿佛仍能闻到天外茫崖的矿尘味。顾锁英笔下的风,是有形的——它卷着沙、裹着雪,雕刻着西部之西的山川;也是无形的——它藏在文字里,带着老一辈茫崖人的记忆,吹过青海,吹过江南,吹向祖国的四面八方。
这风,是茫崖的风,是柴达木的风,更是一代人的精神之风。愿更多人能读到这本书,在风的絮语里,读懂大西北那片神奇土地的过去与现在,读懂那些“被漠风吻过的南飞雁”,如何在盆地岁月的荒芜里,绽放出最强韧、最美好的生命力。
甘建华,生于1963年8月18日,湖南衡阳人,曾在青海高原读书、生活、工作11年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。高级编辑,文化学者,地理学教授,书画鉴藏家,诗文编选家。出版文学、新闻专著及配套评论集三十余部,主编文化地理诗文选本多部并有理论建树,作品入选海内外上百个权威选本。
上一篇: 想起我的老妈妈(原创歌词)
下一篇: 举头遥见潇湘雁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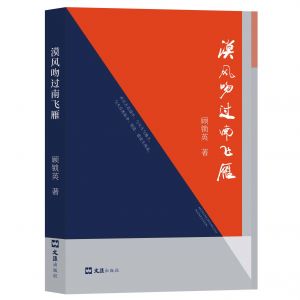

评论[0条]
更多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