函授岁月
体育活动中心欢声笑语,快乐满溢而出,银球飞舞乐无边,技艺切磋乐意浓浓。回家途中,小雨缓缓飘落,弥漫着清新的气息,轻轻落在肌肤上,仿佛一种温暖的抚慰。晚餐的香气、味道与口感,宛如一篇动人的乐章,令人陶醉。夜幕降临,我漫进心灵栖息之地书房,轻轻地摩挲着猩红色封皮,某师范学校中师函授毕业证书,反射出温暖而柔和的光晕。
四十年前岁月如梦如幻,冲刷了记忆的棱角,却留下了珍贵的沉淀。
1979年秋季,城关二小的一个教室里,教师会议气氛热烈、秩序井然,校长目光扫过全场,声音沉稳有力:“新学期迎来了人事调整,原教导主任XXX,因工作需要,调新创办的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,经研究决定,任命XXX老师为新教导主任”,会议结束,阳光透过窗户,洒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开学一个月后,中师函授学习的通知,贴在校布告栏上,我却被副校长唤去东门盂溪滩地建预制场。
当年考虑自己调入本校只满一年,初来乍到,应该以破茧成蝶的姿态完成蜕变,犹如春笋珍惜每滴雨露。函授课本只能枕在夜露里翻阅,双手先练习与水泥砂石对话的技能。
1979年冬天的美景,宛如人间仙境,冰雪覆盖黄湖村大地,闪烁着清冷的光辉,寒风凌厉,漫天飞舞。
母亲盼望着我能在元旦,步入婚姻殿堂,心中充满喜悦和骄傲。婚礼前几天的下午,母亲执意亲手布置婚房,用原本视为废料的笋壳,蘸石灰粉涂抹泥墙婚房,经母亲精致加工,婚房氛围充满了浪漫与温馨。然而,母亲抹墙的双手,被碱水灼得通红时,眼泪从皱纹里淌成溪流。
翌年,母亲查出食道癌时,紫云英正开满盂溪两岸。
我二十五元的工资,攥在掌心,像攥着一把滚烫的沙。带母亲去照相馆拍摄生平第一张照片,摄影师喊“笑一笑”时,母亲枯瘦的手正按着疼痛的胸口。
二月春风还带着料峭寒意,沉睡的土壤已经悄然苏醒。我和母亲,在黄湖山上种马铃薯,俯瞰山下村庄,炊烟袅袅,似梦幻般的色彩,渐渐弥漫村庄上空,与晚霞相互辉映。 母亲说:“我这种病,将来就是饿死的,人活到一百岁也要回去”,山风卷走我的哽咽,却卷不走母亲眼里如水的平静。
妻子身怀六甲的那个黄昏,母亲躺在堂前间黄泥地草蓆上,让我喂她最后三口白糖水,呼出的气息轻得像蒲公英的绒毛:“我要回去了,管顾下代脚手健...”遗言,混着新生儿的胎动,1980年的旧宅里,妊娠的喜悦与丧母的悲痛同时降临,妻子腹中胎儿的新生与母亲生命的消逝,母亲离去的那扇悲伤之门关上了,孩子到来的希望之窗也即将打开,如同黑暗与光明的交界。
此后每个夜办公的晚上,我脚踏车碾过九公里山路时,总觉得母亲化作了头顶的星星。
一眨眼就过去了数年,城关镇函授班学员团队如沙漏,上半截的喧嚣,终将沉淀为下半截的寂静。下赵巷教师进修学校,从蓝图到实景,新楼矗立。中师函授学习,初期以乡镇为单位组织教学,后期因学员数量减少,调整数个乡镇学员,暑期集中学习。
夏季高温闷热,抢收早稻,稻桶泥水飞溅,浑身湿透,弯腰抢种晚稻,汗透衣杉。
暑期,我种植完晚稻,田间管理,只能交妻子和继父承担,自己参加中师函授学习。
城关二小四合院,木楼梯如同一部厚重的历史典籍,每一级台阶,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。我居住在四合院二楼。
午后,我正准备去进修学校听课,走完楼梯抬头时,方形天井阳光斜射而入,天井斜对面,村里一男人,骑自行车驶入四合院,后座坐着我妻子。
始末缘由,原来是我妻子和继父,上午在责任田耘草,中午回家时,在黄湖岭走下坡时,被过路人一辆自行车撞伤了。妻子脸颊以肉眼可见膨胀,右眼脸被顶得微微隆起,仿佛樱桃卡在皮下,颧骨上方淤青,我只能带遍体鳞伤的妻子去医院……。
40年后,我抚着毕业证书褶皱的纹理,忽然懂得中师函授,真正的课本,原来是用建预制场的铁锹、母亲临终的白糖水、继父和妻子弯着腰,在稻稞间一下一下耘田、汗珠掉进浑水里、溅起小小的涟漪写成。
岁月如白驹过隙,逆境中的挣扎和痛苦,终究随着时间的推移,化作笑颜绽放的喜悦,如同盂溪水终将流入灵江,所有坚守都将在时间深处,泛起粼粼波光。
注:中国作家网首发,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版权所有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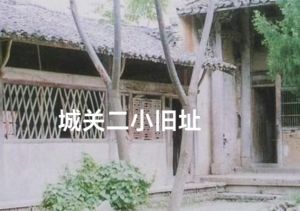






评论[0条]
更多>